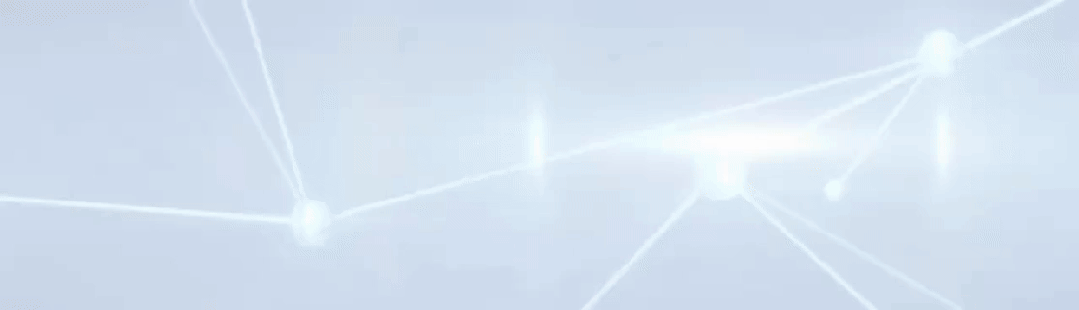
近日,云南省保山市的一起交通肇事案经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涉及交通事故中的“逃逸”、“二次碾压”、责任分担等常见问题。本案因“醉鬼拍车”而起,法院的裁判结果也在社会公众之间形成巨大争议。

法院判决认定,2024年3月25日2时35分,花某驾驶云MZ***7号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沿隆阳区新闻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新闻路与永昌路交叉口以东90米处,遇到沿新闻路由北向南跨越中心隔离护栏停留于机动车道内站立在花某所驾车行驶方向前方的被害人李某,花某减速行驶避让,避让中李某用手连续拉拽、拍打花某所驾车辆的门手把及车窗、车门,花某随即驾车加速行驶,李某随后被该车左后轮碾压,造成李某倒地并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李某受伤倒地后躺于路上,花某驾车沿新闻路由西向东驶离现场。
当日2时37分,朱某驾车(第二辆)途经此事故现场,看到李某身体躺于新闻路由西向东的道路内,朱某随即在前方路口掉头驶回现场,电话报警,并下车对此路行驶过往的车辆进行安全行驶提示。
当日2时44分,花某驾车返回现场,将车停放于现场道路北侧路边,下车与朱某交谈。
当日2时46分许,李某非饮酒后驾驶云ML***2号长安牌小型轿车(第三辆)沿新闻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新闻路与永昌路交叉口以东李某躺倒在地的位置,朱某见状立即上前提示但未果,李某非驾车碾压躺于道路内的李某,造成李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李某非报警。后花某驾车离开现场,并于当日4时1分报警。后民警电话通知花某到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配合事故调查,2024年3月25日12时许,花某到达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经分别鉴定,花某所驾驶的云MZ***7号车肇事时的行驶速度约为32km/h;李某非所驾驶的云ML***2号车肇事前的行驶速度约为53km/h;死者李某系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送检的李某血样(检材)定性检验检测出乙醇,定量检验检测含量为176.03mg/100ml;送检的李某非血样(检材)定性检验检测出乙醇,定量检验检测含量为79.11mg/100ml;送检的云ML***2底盘前部血迹、底盘后部血迹中检出人血成分;云MZ***7左后轮胎面拭子、左后门窗拭子、左前门窗拭子、左后轮内侧拭子、右后保险杆拭子、右后挡泥板拭子中均未检出人血成分;送检的云ML***2底盘前部血迹、底盘后部血迹中检出的人DNA,与李某血样在D3S1358等31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率为2.08×10;送检的云MZ***7左后轮胎面拭子、左后门窗拭子、左前门窗拭子、左后轮内侧拭子、右后保险杆拭子、右后挡泥板拭子中均未检出人DNA。

案发后,经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认定,花某未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而是驾驶车辆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李某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夜间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未降低行驶速度减速慢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交警依法认定花某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李某非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后花某和李某家属对前述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申请对交通事故认定进行复核,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复核后予以维持。

隆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花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未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而是驾驶车辆逃逸,因而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花某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法院认为花某与李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李某头部受伤流血,倒地后无法行动,根据尸体检验意见书,李某系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但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李某的致命损伤是发生于前事故还是后事故,即不能排除李某在前事故中头部已受到致命损伤,即使得到及时的救治也不能挽救其生命的情形存在,故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对该指控未予支持。同时花某的逃逸行为已作为其入罪情节予以评价,在量刑时不应再作为加重情节予以重复评价。鉴于被告人花某已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2025年9月30日,隆阳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花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赔偿被害人家属相应经济损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某非赔偿被害人家属相应经济损失。
一审宣判后,花某和李某非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2月10日,保山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和法院均认定花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和抢救伤员,而是驾驶车辆逃逸,并据此认定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花某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逃逸”、花某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花某是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均值得探讨。

《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花某在发现李某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并停留在机动车道内后,就已经减速行驶进行避让,其速度经鉴定也只有32km/h,符合安全要求。但李某在严重醉酒状态下,不仅违规跨越隔离护栏进入机动车道,还在花某减速的情况下连续拉拽、拍打花某所驾车辆的门手把及车窗、车门,对其持续滋扰。
有意见认为,李某拍打车窗等行为属于一般骚扰,未对花某车辆及人身安全造成紧迫、严重威胁,花某加速驶离并非制止侵害或者避免危险的必要手段。
但本案事发时间是凌晨2点35分,光线不佳、人流稀少,花某在单独驾车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李某的行为意图,以及李某是否携带工具、是否有同伙等其他可能危险,面对这种突发情况,花某出于保证其车辆和人身安全的本能而加速驶离现场,是符合一般人的应激反应的,其行为并不是没有保障安全驾驶的违章,而是具有紧急避险的意图和性质。
而且,即使法院认定的事实中也明确,是在花某加速行驶后,李某才被车辆左后轮碾压,因此花某是为了躲避李某可能的潜在危险才加速驶离,而不是在发生事故后才加速逃离,其不具有逃逸的意图。

交通管理部门和法院均认定花某驶离现场的行为属于“逃逸”,但构成逃逸的基本前提是行为人“明知”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仍然故意逃离现场以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追究。
本案中法院认定,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花某减速行驶后加速行驶,李某在车辆左侧跟着车跑,后翻滚倒地,此时花某驾驶的车辆颠簸了一下。但花某所驾驶的云MZ***7轿车的左后轮胎面拭子、左后门窗拭子、左前门窗拭子、左后轮内侧拭子、右后保险杆拭子、右后挡泥板拭子中均未检出人血成分和人DNA,不能表明李某与花某驾驶车辆发生实质性严重碰撞和碾压。
在起初供述中,花某称事发时感觉到自己的车辆右后轮有颠簸的感觉,但其后面又称,不能排除这种颠簸不是来自被害人,而是源于其他障碍物。
根据监控视频,李某是在左侧跟车跑,即使其倒地后被花某驾驶的车辆碾压,也只可能是左后轮有颠簸,而花某是感觉右后轮有颠簸的感觉,不可能意识到是压到了在车辆左侧的李某,而仅仅通过监控视频能够直接显示的车辆颠簸,也不能确认是哪一侧车轮碰到了障碍物才导致。因此,根据监控视频、拭子鉴定和花某最初的供述,实际上并不能确认是花某的车辆导致李某倒地受伤或者进行了碾压。
在当时光线不佳,花某又因高度紧张加速驶离现场的情况下,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没有看到或者意识到位于车辆后方李某倒地或者压到李某都是正常的,难以直接认定花某明知已经造成交通事故才逃离;其在驶离现场后,过几分钟后才返回确认是否与李某发生接触也是正常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三条和第五条均表明,“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简称“《程序规定》”)第一百二十条则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是一种隐瞒肇事者身份的行为,其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在现场藏匿的行为(让他人顶包等),而其逃避法律追究的本质,则是在能够救助被害人和配合办案机关调查的前提下,拒绝或者逃避履行相关义务。
在本案中,一方面,花某是否“明知”已经造成李某受伤倒地是不确定的,因此其在第一次驶离现场时,是否具有不履行救助被害人义务的故意也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花某驾车经过事发地点是在2时35分,其加速驶离现场后,又在不到10分钟后返回,并停车与已经电话报警的朱某交谈。花某返回现场仅2分钟,李某非就驾车碾压李某致其当场死亡,直到李某非报警后,花某才驾车离开,并在4时1分也报警,后又经电话通知到交通管理部门配合事故调查。
从花某第一次返回现场的时间间隔、停留在现场与报警人交谈、之后自己主动报警和配合调查来看,其第一次驶离现场更多是出于被李某拉拽、拍打车辆后的害怕、恐慌等心理,难以确认花某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使花某有驾车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也不足以认定为 “逃逸”。

本案中,从时间、空间及因果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李某可能先后遭受两次碾压,因而可能涉及“两次事故”。其中第二次李某非驾车碾压李某,并造成李某当场死亡是确定的;而关于第一次花某驾车是否碾压到李某,如果仅根据监控视频和花某最初供述所称的“右后轮颠簸”,以及花某车辆上提取的未检测出人血成分和人DNA的拭子,是无法排除“颠簸”是碰到其他障碍物的合理怀疑的。而且,李某倒地是因为其用手拉拽、拍打花某驾驶的车辆时被“带倒”或者“碰倒”,还是因为其严重醉酒导致自己站立不稳而“摔倒”,实际上也是难以确定的。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花某“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法院根据尸体检验意见书等,最终认定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李某的致命损伤是发生于前事故还是后事故,不能排除李某在前事故中头部已受到致命损伤,即使得到及时的救治也不能挽救其生命的情形存在,故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
一方面,法院以不能确认李某的致命损伤是由花某还是李某非造成,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认定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是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的;但另一方面,法院只审查花某是否可能造成李某直接死亡,却没有对李某非驾车碾压的行为是否直接造成李某死亡、对死亡结果的影响等进行充分审查。
在本案中,花某和李某非驾车经过现场的时间相隔11分钟,而两次事故中可能的侵权主体、违法行为完全不同,在花某和李某非没有共同故意或过失,不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况下,应分别具体认定责任。法院判决将两次事故混为一谈,只审查花某行为的可能结果,但没有详细区分花某和李某非的行为对李某死亡结果的原因力大小,直接认定“共同造成死亡结果”,忽略了两次事故的不同影响,实际上是事实不清的,而且似是将该结果更多地归责于花某,明显不当加重了花某的责任。

本案中,虽然花某的行为可能导致李某倒地受伤,从而成为李某被李某非驾车碾压的前提,但从因果关系而言,李某非的行为应当属于相对独立的介入因素,其不仅具有突发性和异常性,而且还可能是直接造成李某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应当否定或者至少减弱花某的行为与李某被“二次碾压”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异常介入因素可能阻断因果关系,而如果介入因素的发生和介入,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经预见或者基于经验法则能够合理预见的,则属于正常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首先,李某非是明显的酒后驾车,且其血液酒精含量几乎已经达到“醉驾”的程度,属于严重的违法驾驶,其行为性质“明显异常”。
其次,事发地点位于保山市隆阳区新闻路,相关信息显示该道路是双向四车道的非封闭城市临街道路,而李某非在凌晨2点多的行驶速度为53km/h,明显较快,即使在朱某上前提示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减速迹象,其不当驾驶行为显然也与其饮酒有重要关系。
第三,从李某倒地到其被李某非驾车碾压,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朱某在李某倒地后2分钟左右驾车经过,后又返回现场和报警,并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提示,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驾驶人可以主动发现或者避让倒在车道内的李某,避免对李某的后续伤害;而且,从朱某对过往车辆进行提示到李某非驾车碾压李某,有9分钟的时间,其间也有其他车辆经过,但都没有对李某造成伤害,也表明正常情况下朱某的提示是有效的。但在李某非酒后驾车的情况下,朱某提示未果,最终李某非驾车碾压李某并造成其当场死亡。在驾驶人可以主动发现,也有其他人员予以有效提示的情况下,李某非仍然没有采取任何减速和避让措施,显然也是明显异常的。
本案事发时间是凌晨2-3点,虽然光线环境可能相对昏暗,但道路车辆和行人也同样稀少,正常情况下在无遮挡物的情况下,驾驶人对前方有人躺在地上是能清楚判断的。但李某非在饮酒状态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李某的情况,也对朱某的提示毫无反应,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超出花某、朱某等人的预见可能性,其作为介入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并直接导致李某当场死亡,应当阻断或者至少大幅减弱花某行为与李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花某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前是正常行驶,且进行了减速避让,符合驾驶规范,后因李某严重醉酒后的连续滋扰行为,花某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加速驶离。
虽然李某倒地发生在花某加速之后,但关于李某倒地是否就是花某驾车造成的,花某本人否认,也没有直接的监控录像予以证明,其他证据也不足以完全排除李某因醉酒而自行摔倒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李某是在花某加速后,因与车辆接触才倒地,也是李某自己在醉酒后上前主动接触,而且其是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护栏后,在机动车道内连续对车辆进行拉拽和拍打,明显存在重大过错。
《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本案中,如果李某是因自己严重醉酒站立不稳而摔倒,则花某在法律上实际不负有任何救助义务,应由李某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李某是因花某加速驶离时,与车辆接触而倒地,花某加速驶离也是因李某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并对其进行连续滋扰才实施的躲避行为,花某加速驶离即使不当,其过错程度也明显轻微,而李某自己醉酒后的违法行为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或者至少是主要责任。

本案中,李某可能因两次事故而被“二次碾压”,而且法院明确认定,是李某非酒后驾车经过事发道路,经朱某提示未果后,碾压李某并造成其当场死亡。
从违法性而言,李某非酒后违法驾驶的行为是故意,对碾压李某的结果也至少存在重大过失,具有高度可责性。
花某存在两次驶离现场的行为,其中第一次是为了躲避李某严重醉酒后的连续滋扰行为而加速驶离,并且花某在李某非驾车到现场前就已经返回,李某因被李某非驾车碾压而当场死亡的结果,与花某第一次驶离现场的行为之间,实际已经因花某返回现场而阻断,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而花某第二次离开现场,是在李某非报警后,此时李某已经当场死亡,其死亡结果与花某离开的行为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因此,花某虽然存在两次离开现场的行为,但客观上都与李某非酒后驾车碾压李某并致其当场死亡不具有关联性。
法院认定“不能证实李某的致命损伤是发生于前事故还是后事故”,因而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但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仅应当否定花某对李某死亡结果的直接责任,而且在死亡结果可能由花某和李某非共同造成的情况下,在因果关系及其影响程度无法查明时,花某至多只应与同样作为驾驶人的李某非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
但在本案中,在李某非存在酒后驾车的严重违法行为,应当对第二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可能单独对李某的死亡结果承担直接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却仅认定李某非为次要责任,反而认定花某为主要责任,难以体现过错与责任的相当性。

保山市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花某属于“逃逸”,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但该责任认定实际上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和《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的“推定”,是一种行政违法责任的“拟制”,但不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事实”。
刘某立涉嫌交通肇事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642号)也表明,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意见可以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依据。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考虑了事后逃逸等情节,因而与事故发生时各方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发生严重偏差,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刑事领域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判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是人民法院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依据,但并不能直接代替刑法意义上事故责任的判断。
在本案中,保山市交通管理部门实际也是以“逃逸”作为“推定”花某对全部可能的两次事故所最终造成的李某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但结合所有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花某加速驶离现场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中涉及李某本人严重醉酒后的违法行为、李某具体死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李某非酒后违法驾驶并直接导致李某当场死亡等多种复杂因素,而且李某和李某非的违法和过错程度显然都较花某更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对花某是否应当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不应简单以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认定为依据,而应当根据对李某死亡结果发生的客观原因力大小,对因果关系和责任分担进行实质审查和判断。
在李某涉及两次可能事故,而关键死因又难以直接查明的情况下,花某与李某非同样作为驾驶人,且其违法程度明显较酒后驾驶的李某非更轻,花某至多只应与李某非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而在被害人李某也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花某更应当只承担次要责任,至多只承担同等责任。

法院认为,花某的行为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同时花某的逃逸行为已作为其入罪情节予以评价,在量刑时不应再作为加重情节予以重复评价,结合其赔偿被害人家属和取得谅解等情况,判决花某犯交通肇事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法院关于花某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也不对其逃逸情节重复评价的裁判值得肯定,但其最终结果仍存在问题。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量刑档次,涉及基本犯罪构成、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在本案中,法院否定了花某“逃逸”属于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而将其作为基本犯罪构成。
然而,首先,如前所述,本案中花某是否“明知”在躲避李某连续滋扰的过程中,加速驶离时已经导致李某倒地受伤,以及是否具有“逃逸”尤其是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和目的的证据并不完全充分,不足以认定其属于“逃逸”。
其次,根据《解释》第二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包括“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和“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
因此,“逃逸”作为基本犯罪构成存在于“一人至两人重伤”的情形,而在“死亡一人”的情形下,“逃逸”实际只能作为情节加重构成,并不具备将“逃逸”作为基本犯罪构成的条件,法院将其作为入罪情节实际上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根据刘某立涉嫌交通肇事案的裁判理由,即使花某的行为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逃逸”,在进行刑法评价时,仍然需要根据该行为对最终伤亡结果的原因力大小进行实质判断。而在本案中,花某驶离现场的行为,与李某非碾压李某并致其当场死亡的结果,已经不具有客观上的实质联系,即使认定其“逃逸”,也只是行政认定,但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更不应当将“逃逸”作为花某的基本犯罪构成。
最后,本案中即使花某加速驶离的行为存在不当,但李某和李某非都存在严重违法,而且花某的过错程度相较而言明显更低,也不应当由花某承担主要责任,至多只能是三人承担同等责任,在只造成死亡一人的情况下,花某即使承担同等责任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因此,法院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认定花某属于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主要责任,并判决其构成交通肇事罪,与法律规定、客观情况和刑事案件的实质审理要求均不相符。

本案中,法院可能试图通过强化驾驶员的救助义务来维护道路安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自身的重大过错、后车的独立侵权和严重违法行为,以及驾驶人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急困境和心理状态,导致与公众的朴素认知产生偏差,形成舆论的巨大争议。
作者简介
.
杨琪琛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管理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实践导师,矿业权评估师、高级企业合规师,具有证券和期货从业资格。在北京市检察机关和区委组织部门工作多年,参与办理各类案件数百件,包括侵犯财产犯罪、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性犯罪、赌博犯罪、毒品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强制医疗程序案件等,拥有丰富的刑事司法实务经验。
执业以来,办理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涉矿犯罪等各类重大复杂案件,多个案件取得不起诉、撤销或者改变指控、从轻减轻处罚等辩护效果
业务领域:
刑事辩护、申诉和控告以及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编辑、排版:王昕
审核:管委会


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17层
武汉分所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国际中心10层1001室
相关资讯
2026-01-28
2026-01-26
2026-01-23
2026-01-22
2026-01-21
2026-01-20



